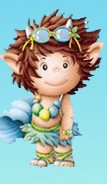鋼鐵博客 彩虹
| 歡迎登陸博客 彩虹的辯論 |
主人信息
彩虹(公開)
Blog主人:彩虹
Blog分類:休閑娛樂類
Blog積分:73645.9
日志數(shù)量:882
開啟時間:2006-07-20
瀏覽次數(shù):597822
評論數(shù)量:3
最后更新:2016-04-29
Blog分類:休閑娛樂類
Blog積分:73645.9
日志數(shù)量:882
開啟時間:2006-07-20
瀏覽次數(shù):597822
評論數(shù)量:3
最后更新:2016-04-29
最新文章
| ·最新觀測一個超級黑洞其質(zhì)量是... |
| ·告別山寨大國 中國輸出創(chuàng)新時代... |
| ·他是全國最小黑客,8歲寫代碼,... |
| ·從資本支出的角度講 5G發(fā)展要靠... |
| ·Uber重申小費(fèi)政策:無需支付 也... |
| ·舊手機(jī)過海關(guān)居然讓交稅?國外... |
| ·這個國家 窮得連印鈔票的紙都買... |
| ·水泥業(yè)遇10年來最嚴(yán)酷寒冬 “水... |
| ·大地震證明日本制造依然強(qiáng)大?... |
| ·去年中國家庭人均財富144197元... |
最新評論
|
· 內(nèi)容:好象快成熟了!
|
|
(2007-06-02 18:30) |
|
(2006-08-03 16:47) |
|
(2006-07-31 17:49) |
日歷
| << < 2025年11月 > >> | 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|
|
最新辯論
| ·為啥分析師不做讓你做? |
| ·現(xiàn)在是不是鋼材銷售轉(zhuǎn)型時代... |
| ·現(xiàn)在的型鋼市場還能漲價到什... |
| ·如果明年鐵礦石繼續(xù)漲價,鋼... |
| ·寶鋼是不是“白眼狼”? |
| ·鋼材過剩億噸不減產(chǎn) 鋼企明年... |
| ·二季度鋼市將如何演變~~ |
| ·鋼材期貨在國內(nèi)是否能成功 |
最新blog
| ·金屬世界博覽展組委會 |
| ·FZLbxg |
| ·噪聲治理 |
| ·云A鋼兆鋼材 |
| ·sdadwqwe |
| ·大明看盤的 Blog |
熱門辯論
| ·“保就業(yè)”還是“保工資”? |
| ·什么原因造成了節(jié)后市場價格... |
| ·先有雞還是先有雞蛋? |
| ·如何看待寶鋼四季度價格政策... |
| ·下半年宏觀經(jīng)濟(jì)政策取向?qū)?.. |
| ·關(guān)于2006年12月份至明年3月份... |
| ·人性本惡還是人性本善 |
| ·鋼材過剩億噸不減產(chǎn) 鋼企明年... |
Blog排名
| ·鋼市采風(fēng) |
| ·啦啦風(fēng)鷂的博客 |
| ·金鱗 |
| ·綠幻藍(lán)想 |
| ·歡樂調(diào)頻 |
| ·I虎氣沖天 |
| 熱門文章TOP10 | 更多 |
最新日志
| 總?cè)藬?shù)247位 會員數(shù)0位 游客數(shù)247位 |
國軍上將如何看汪精衛(wèi)做漢奸
圖注:1938年汪精衛(wèi)發(fā)表《對中日關(guān)系之根本觀念及前進(jìn)目標(biāo)》
短史記第187期
一、徐永昌曾指責(zé)張學(xué)良:不能踏實(shí)做實(shí)地工作,卻日日喊叫抗日
汪精衛(wèi)以國民黨副總裁之身份,于1938年末自重慶秘密出走,稍后并在日軍支持下于淪陷區(qū)成立汪偽政權(quán),自此走上了無法回頭的漢奸之路。而在1938年初,汪氏的“對日和談”立場,還曾一度被諸多國民黨要員如徐永昌等人寄予厚望。
抗戰(zhàn)期間,徐永昌深受蔣介石重用,長期擔(dān)任軍令部部長之要職,參謀戎機(jī);后獲授陸軍一級上將。關(guān)于對日“和”、“戰(zhàn)”,徐氏有自己獨(dú)特的認(rèn)知。譬如,他曾在日記中批評張學(xué)良,說他“對抗日的實(shí)地工作,不能踏實(shí)去做,卻日日時時在喊叫抗日,甚至糾合狂叫者吼喊抗日,此真時髦病與狂妄病”;對當(dāng)日主導(dǎo)報刊輿論,鼓吹立即對日開戰(zhàn)的知識分子,徐氏的評價是“見解淺浮、偏激、執(zhí)拗、誕妄,較之義和團(tuán)時代并不進(jìn)步”。①
徐氏的這種批評意見,源自其對當(dāng)日國民政府國防實(shí)力的切實(shí)認(rèn)知——1937年8月7日,國民政府召集軍政大員及地方派系領(lǐng)袖至南京參加“國防會議”。會議雖決定積極備戰(zhàn)并堅決抗戰(zhàn),但參謀本部給出的武器與彈藥估算總量,卻僅夠6個月之用,至于巨額軍費(fèi),更尚全然沒有著落。②
故抗戰(zhàn)全面爆發(fā)后,徐氏仍未放棄游說蔣介石繼續(xù)對日“和談”。1938年初,徐氏曾致函蔣,認(rèn)為“敵人狂焰,猝難遏止,國際參戰(zhàn),杳不可期”,“若不自尋緩和途徑,……萬一武漢不支,我再西退,……將來欲圖挽救,益難為功”,希望當(dāng)局能夠“乘敵和戰(zhàn)意見不一之時,與之周旋談判,使敵之主和派得以牽制軍閥,而我則藉資延宕”,和談若成,對中國自當(dāng)有利,和談不成,亦可獲得喘息之機(jī)整軍再戰(zhàn)。③
概而言之,徐氏在1938年初的意見是:“決對堅持長期抗戰(zhàn)則危險太大(全國無能戰(zhàn)之軍)。若質(zhì)直言和亦萬難做通”,故今日之事惟有“延宕”二字。基于此種認(rèn)知,徐氏一再致電蔣介石,希望能開啟對日和談,且明言:“和不必有成,但能延宕下去即是大利。”④
國軍上將如何看汪精衛(wèi)做漢奸
圖注:汪偽政府時期之汪精衛(wèi)
二、汪精衛(wèi)出走,徐永昌評價稱:于國家有小損,于抗戰(zhàn)無損
值得指出的是,當(dāng)日與徐永昌持相似意見者甚多。如七七事變后,閻錫山曾一度堅決主戰(zhàn),且號召與中共之八路軍積極合作;但隨著南京的失陷,閻氏的看法亦發(fā)生了改變。1937年12月,閻氏前往漢口參加國防會議,曾詢問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:“中國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協(xié)定如何?日如允中國加入,自須平等待我;否則,可以證明日之侵我,非為防共”——日本侵略中國,一再以“防共”為辭;故閻氏提議中國不如加入德意日之軸心國同盟。陳立夫、戴季陶等亦向陶德曼提出:“讓日本、德國、中國聯(lián)合起來,先把蘇俄打垮。”⑤
具體到主持對日和談的人選,徐永昌認(rèn)為非汪精衛(wèi)莫屬。據(jù)徐氏1938年1月15日的日記,1月13日,他曾與汪有過一次很深入的談話:
“前日與汪先生討論延宕問題。余以此事萬不可令蔣先生負(fù)責(zé)。緣此等時期設(shè)蔣先生因此搖動其政治地(位),直無異顛覆國家。汪先生極是余說(最好是汪先生負(fù)責(zé)進(jìn)行)。渠之有此資格。”——最末六字,在徐日記原文中被劃掉。同日,日記上部空白處,徐還寫有“汪可負(fù)責(zé)。不可任蔣先生負(fù)責(zé)和”等字樣。⑥
徐永昌這番意見,頗欲以蔣在明,以維系堅決抗戰(zhàn)之民心;以汪在暗,以收和談延宕之實(shí)利。雖然據(jù)其自述,該意見得到了汪精衛(wèi)的贊同(汪先生極是余說),但事實(shí)上,因種種原因,汪并不甘于僅做蔣的影子,最后終于選擇了走上臺面,出走重慶。徐氏所謂“和不必有成”,在汪氏的立場,也變成了“和必須有成”。
汪精衛(wèi)出走后,蔣曾就其影響所及,征詢徐的意見,徐的回答是:汪氏此舉,“于國家有小損,于汪先生個人有大損,于抗戰(zhàn)無損”。⑦徐氏該評語是否準(zhǔn)確,自可見仁見智。然有損無益之評語,已足以表明,即便主張對日和談如徐永昌者,亦不能接受汪氏此舉。今人評價汪氏之歷史功過,徐永昌這番立場,可供參考。
注釋:
①(臺)胡春惠:《汪精衛(wèi)與“低調(diào)俱樂部”》,《抗日戰(zhàn)爭研究》1999年第1期。②國防聯(lián)席會議記錄(1937年8月7日),參謀本部速記。③(臺)中研院:《徐永昌先生函電言論集》,P62。④徐永昌日記,第四冊,P215。⑤(臺)蔣永敬:《汪精衛(wèi)的“恐共”與“投日”》,《抗日戰(zhàn)爭研究》1999年第1期。⑥徐永昌日記,第四冊,P216。⑦徐永昌日記,第五冊,P2。

不 經(jīng) 歷 風(fēng) 雨 怎 么 見 彩 虹!
※ ※ ※ 本文純屬【彩虹】個人意見,與【鋼之家鋼鐵博客】立場無關(guān).※ ※ ※
 該日志尚無評論! 該日志尚無評論! |
Copyright© 2004-.SteelHome.cn. All Rights Reserved
上海鋼之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版權(quán)所有
地址:上海市東方路818號眾城大廈23樓 郵編:200122
客服電話:021-50581010(總機(jī)) 4008115058
上海鋼之家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版權(quán)所有
地址:上海市東方路818號眾城大廈23樓 郵編:200122
客服電話:021-50581010(總機(jī)) 4008115058